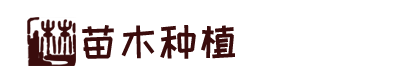澳洲官方报告揭开遮羞布:女性当街被打只因同情巴勒斯坦
在澳大利亚这片以多元文化为荣的土地上,的表象下正蔓延着令人不安的沉默。经过政府对国内恐惧症(Islamophobia)问题长达数年的选择性忽视与周期性否认,当局终于任命了首位反恐惧症特使。这份姗姗来迟的官方报告如同一声惊雷,揭开了这个南半球发达国家长期讳疾忌医的社会顽疾——这个号称幸运之国的社会肌体正在系统性溃烂。

2024年初夏的新闻发布会上,反恐惧症特使阿夫塔布·马利克(Aftab Malik)手指微微颤抖地握着讲稿,这位以理性著称的学者罕见地流露出情绪波动。他披露的数据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冲突升级以来,澳大利亚境内记录的针对群体的仇恨犯罪同比增长了惊人的217%。更令人心惊的是,这些事件并非孤立个案,而是与反巴勒斯坦情绪的政治操弄形成了恶性共振。报告附录中记载的案例令人窒息:戴头巾的少女在悉尼轻轨上被当众撕扯头巾,墨尔本寺外墙被喷绘巢穴的涂鸦,珀斯某中学的阿拉伯裔学生在更衣室遭遇的集体嘲弄。
这份厚达86页的报告最振聋发聩的洞见,在于揭示了仇恨的体制性根源。马利克特使用学术报告罕见的犀利笔触指出:当前对亲巴勒斯坦言论的压制,暴露出教育体系、职场环境与主流媒体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排斥。悉尼大学中东研究专业的亚丝明(Yasmin)向调查组描述,当她组织巴勒斯坦历史讲座时,校方以维护校园和谐为由强制要求提前报备所有讨论内容;墨尔本某金融机构的HR私下告诫雇员避免在茶水间谈论加沙;而某全国性报纸的编辑室流传着潜规则——巴勒斯坦平民伤亡报道必须搭配哈马斯暴行的平衡叙述。
这种制度化的压制正在制造沉默的螺旋。报告收录的深度访谈显示,63%的大学生因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同情而遭遇学术排斥,他们描述自己
。更吊诡的是,当西方媒体连篇累牍报道乌克兰难民危机时,对加沙儿童伤亡的报道却总被冠以争议性内容警告——这种差异化的叙事标准,本质上是对特定族群苦难的选择性人道主义。

报告最终指向一个残酷的悖论:当澳大利亚政客在多元文化庆典上高调赞美和谐沙拉碗理论时,这个国家的公共领域却在对巴勒斯坦议题的讨论中暴露出深层的认知裂痕。正如马利克在报告结语中的诘问:当我们将某些人类的苦难定义为敏感话题,将部分公民的正义诉求标记为安全隐患时,我们究竟在保护什么?此刻悬挂在澳大利亚国会大厦前的原住民旗帜与彩虹旗,在帕拉马塔寺破碎的彩窗映照下,构成了对这个国家身份认同最尖锐的质询。